前 言
十年前的11月26-28日,寻找航标:2010“海上影展暨论坛”在上海顺利举行。本次影展由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和上海影视文献图书馆联合主办,同济影像论坛承办,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一,神奇现实:纪录片单元,包括《算命》、《哈尔滨旋转楼梯》、《龙哥》、《小李子》、《1428》、《喉舌》、《小人国》、《音乐人生》、《众生》、《火星幺宗合症》、《借我一生II》等2009年以来最新纪录片11部;
二,向现实致敬:剧情片单元,包括《好猫》、《八卦》两部体现魔幻现实的剧情长片;
三,电影圆桌:“方法的焦虑”纪录片论坛,来自全国各地的纪录片专家和导演,如司徒兆敦、张献民、张同道、郭熙志、徐童、周浩、于广义、张钊维、符新华等齐聚上海,与上海本地纪录片人一起,就纪录片的文体、伦理与方法问题,展开了富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探讨与争鸣,有关成果将陆续在学术刊物发布;
四,多音齐鸣:高校学生短片单元,为包括同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及香港演艺学院等院校在内的学生短片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以下答问来自影展手册。
论坛期间,“海上影展暨论坛“策展人,导演黎小锋与导演徐童展开了一场对谈,十年后,让我们再次回顾这场关于纪录片创作的精彩对话。
注:
问:黎小锋,纪录片导演, “海上影展暨论坛”策展人
答:徐 童, 纪录片《算命》(开幕片)、《麦收》导演
游民纪录片
黎小锋:《麦收》、《算命》与您的文学写作活动有何关联?您把自己的纪录片是看作一个社会学文本,一个艺术作品,还是别的什么?
徐童:我的东西和文学写作有直接的关系。在拍片子之前的很多年里,包括到现在,我一直都在看小说。我们常说,文学即人学;我拍纪录片也拍的是人物,就是这个意思。
纪录片在我看来,不可能是只有一个单一的属性或者功能。如果从我个人的成长背景和喜好来说,我更倾向于它是作品的感觉。比如把其中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思考都会放在里头。纪录片就是真实的虚构,这里头作品感会更明显。但是,这只是倾向于作品,并不是没有,也不可能没有别的东西,你说的社会学文本的属性当然也囊括其中。像从《麦收》到《算命》,不难看出中国游民社会的面貌;人物还是人物,故事还是故事,但是游民的生存处境,游民接人待物的行为方式,就是游民意识,游民文化,也都在片子了呈现出来了。所以说,我更喜欢杂糅一些的东西,更丰富,更有复杂性的东西。

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最后甩出来的“还是别的什么”。我的片子就是我的一段生活实践,一段生活史,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这是我特别看重的东西。生活肯定大于影片;影片只是生活实践的纪录片断。我能够拍什么样的片子,首先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甚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我觉得很重要,这是我片子的根子和命脉所在。所以,前不久和王小鲁聊的时候,小鲁说我是游民拍游民(大意是这样),我觉得他说得挺准,他说出了我身处的位置,和我的生活实践的这个根本的东西。相比作品而言,我更重视这个东西,片子反而好象是一个副产品。
黎小锋:您在纪录片创作中,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电影语言、创作方法、文体风格?总之,您有没有在文体探索方面有过困惑、焦虑?怎么找到自己的道路?
徐童:崔子恩老师曾经说他是低产阶级,他是倾向于无产阶级的低产阶级。我同意他的说法,我也一样,也是低产阶级。怎么说呢,毕竟有个摄像机,有辆车,到处跑,可以拍摄到现在;而给我最大支持的,不是有钱人,而是那些被叫做游民的无产者。所以,我对他们很感激。和他们一起生活和交往的日子里,我不仅拍下了生活的片断,同时,更为吃惊的是那些无处不在的形式感。在他们的生活空间里,在他们的语言中。游民游走在江湖上,自有一套行为方式,谋生技巧,言语说道。像《麦收》里苗苗所说的“生存之道”;《算命》里厉百程讲的“孤单命”,以及唐小雁的江湖遭遇,都有一种天然的形式感。这种东西是浑然天成的,它本来就在那,关键是你有没有把自己扔在里头,体会其中的百般滋味。生活里的形式感无所不在;生活从来就不缺少形式的东西;我感觉,拍纪录片是最不用为形式、语言、文体风格之类发愁或焦虑的事。

黎小锋:实话实说,我在最早的一个纪录短片中曾经尝试采用章回体结构,可惜没有实现。因此,看到《算命》后非常惊喜。您为什么要采取这种传统章回体的结构样式呢?这到底是创新还是倒退?
徐童:王小鲁说《算命》有一个气场;它接通了传统的脉络(大概意思)。游民社会自古有之。自宋代以后,一些“宗法人”由于战乱和人口激增而失去了土地,背井离乡,游走江湖,成为脱离了宗法网络秩序的人,学称“脱序人”,也就是游民。游民为了生存,必须改变“宗法人”日益萎缩的人格,具备主动进击的精神,敢于挑战社会(有关游民社会的研究请参见王学泰先生的著作);千年以来有关游民的故事口口相传,集大成的就是《水浒传》。49年以后,新中国消除了游民(主要是城乡两分法,使城乡隔离),在“大锅饭”的年代,个人被重新固定在体制里,成为和“宗法人”相似的,个性萎缩的“单位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逐渐确立,社会迅速转型,下岗失业人员剧增,“单位人”成为新的“脱序人”(当然还有其他各种不同原因的无业人员),我叫他们是“新游民”。
所以,王小鲁所说的那个“脉络”,实质上就是千年以来的中国游民社会的脉络;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小传统,就是游民文化的脉络。《麦收》《算命》和我的新片《老唐头》,可以说就是新游民社会的缩影。小鲁所说的那个“气场”,实质上就是片中人物身上尚存的古代游民的气息。片中的人物各个都很仗义,因为都明白出门靠朋友的道理;为了生存,他们身上的反社会性格首先对准的就是金钱,正所谓衣食不足不必“知礼节”“知荣辱”,所以,“走偏门”,据帮派,遇事付诸暴力就是游民的显著特征。这就是说《麦收》《算命》和《水浒传》中的人物,拥有相同的游民意识。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讲《算命》拟仿了以《水浒传》为代表的古代章回体的结构形式,它是和游民文学相似的游民纪录片。当然,毕竟时代不同了。这里所说的“拟仿”,又有使用了当代艺术里的“挪用”的手法;致于把这种手法用于纪录片,我想是否可以在当代艺术的语境里加以讨论?我只是有意无意的在这么做了。

新游民脱离了公有体制之后,通过自己奋斗,以博衣食。这样他们必须改变自己原有的性格,从而形成适应社会的性格,否则就会被淘汰。自古游民性格里的一个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反社会性。“因为游民不希望社会稳定,只有社会动乱他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和社会地位。用《沙家浜》胡传魁唱的话说就是“世乱英雄起四方””。我片中的人物和古代的游民相比,似乎缺少了这种豪气,只能说那是因为他们遭受了更为严酷的制度性压迫。但面对生存就是一切的挑战,他们铤而走险,步入偏门,在我的镜头前上演了一幕幕新游民的爱恨情仇。有时候我在想,这种反体制,反制度性压迫的东西,在当下的中国社会里是否具有后现代性?因为,游民社会作为一个隐性的社会,它所对应的当代中国社会是十分荒诞的。有人形容我们像两个错位的航班,一个是迟到的现代主义,一个是早到的后现代主义。《算命》所记录的游民社会以及渗透出来的游民意识,在对抗专制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压迫时,是否可以在我们的传统里找到某种东西,这个传统肯定不是儒家文化那个大传统,而应该是游民文化这个小传统。当然,相反的,也有人说游民意识是现代化的一大障碍,是建立公民社会的绊脚石。我想这些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

“道德底线”问题就像咬屁股的老虎
黎小锋:有人标榜纪录片都是可以给被摄者看的。但《麦收》显然是没法给那些女孩看的。扎得越深,能露出来的越少,您在制作过程中,有没有为以后是否公开、发行产生过犹疑?现在如何解决公开、发行问题?
徐童:我也听说过国外有过类似的说法,就是片子必须给被拍摄者看,并且是立了法的。这事乍一听挺有道理,实际上挺伪善的。好象这么做,你就可以问心无愧了,便可以为所欲为了。那只能是给被拍摄者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我所把握的,还是尽可能的保护被拍摄者。比如划定有限的放映区域和人群。像《麦收》目前是不在大陆发行放映的。《算命》前不久和美国的一家发行公司签了协议,发行的方向主要是大学收藏,大多用于研究。

黎小锋:面对性工作者、八字先生、乞丐、智障这样的底层人士,摄影机稍不留神就构成对他们的窥视甚至侵犯,您怎样把握自己的道德底线?
徐童:拍这类故事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从一开始我就十分渴望过另一种生活;我希望感同身受;我希望用自己脚踏实地的生活实践,开始一段“负罪感”的,宿命般的表达。
你说的“道德底线”问题,就像咬屁股的老虎,这几年追得我挺恼火。既然大家都明白纪录片的原罪,那么片子还是照样拍,还越拍越多,电影节照样办,越办越红火。这不是明知故犯吗!就我个人来说,既然我选择了原罪,这就是宿命,就没有资格去谈论“道德底线”的问题了。因为,这个选择本身就已经在道德底线之下了,还有什么底线可说的?所以说,我无法说“道德底线”是怎么回事,更无法说这条要命的底线应该划在什么地方;我只能谈论自己的感受,说说自己在这条底线下面摸爬滚打的体会。

几年来和我的朋友们生活在一起,让我感同身受的就是四个字:丛林法则。这里头有几个意思:
第一,就是我们常说的,拍摄关系就是人际关系。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基础。说白了就是建立一种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的利益关系;也就是一种交换关系。游民生活在处境艰险的江湖,生存是第一需要,利益关系是个基本的前提;影像就是交换的结果。
第二,就是这个“义”字。朋友相交;义字当头。义就是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只讲帮派,不讲是非。这也是就是帮派性。游民生活在社会底层,是最为弱势的一群,他要向社会索取,没人会乖乖的给他,这样就要扎堆结伙,甚至付诸暴力。厉百程投奔他三弟给人算命,他身有残疾,挣得是开口钱,言语之间左右他人的命运,这般空手套白狼的谋生手段,换个角度讲也该算是软暴力了。“唐小雁棒打无赖汉”,实际上是为了保障小店的安宁,不致影响财路。所以说,裹挟在这样的拍摄关系里,我的片子无法做到所谓的真实;能剪出来看的东西,就是大家说的那个真实的虚构。它的倾向性肯定是站在游民的立场上的;这就是片子所必需担当的那个“义”字。
第三,就是拍摄的野蛮性。新游民是在社会转型中,从公有体制游离出来的,“脱序”后,那种公有体制内的角色意识也就消失了。面对凶险莫测的江湖,为讨衣食,取而代之的就是赤裸裸的野蛮性。在拍摄现场,在义不容辞的拍摄关系里,这种蛮性也渗透到每一个镜头里。所以我说自己,做为身份有些不明的作者,是自甘沉沦在底线之下的。在《麦收》出来后,遭到各种道德质疑,甚至不公,但得以走到今天,我还在继续干新片子的原因,我想是和在游民社会里浸染的那种蛮性,以及抛弃了道德优越感所获得的那份力量分不开的。纪录片本来是应该有点蛮性的东西,但而今,它被道德驯化得十分孱弱。这就像国人自古本来是,衣食不足不必“知礼节”“知荣辱”,本来是应该有点蛮性的民族,但被儒家训练成了“知礼节”“知荣辱”的宗法人。所以说,如果说道德指责如同道德绑架,那么我这几年所干的就是想方设法的去抵抗它,挣脱它;也就是从自己心里头挖掉道德优越感这个东西。这样才能根本上瓦解道德焦虑;还其纪录片本应该有的蛮性特征。在这儿,我还想感谢张献民老师。
我记得那年在“云之南”放映《麦收》的第一场之后。是那天的中午,在省图书馆的楼道理碰见张老师。他说:看见没有?那边门口贴得东西?我说:没看见。他说:是NGO贴得公开信,大概意思是要征集观众签名,取消《麦收》的下一场放映。我当时没整明白是怎么回事,就问张老师NGO是什么?他说是一些社会工作者。我就问张老师应该怎么办?他说:你可以向影展方说明一下,如果不能放映,你可以在自己的住处搞个私人放映,向他们借个影碟机,在门口贴个通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可以向张献民老师求证的。当时,我觉得张老师的意见很切合实际,也很实用,我至今认为他是第一个帮助和支持我的人。

后来,我和易思诚先生原原本本的说了这个意思。易思诚先生很干脆,他说影展不会撤消《麦收》的下一场放映,如果有问题,他兜着。事隔一天之后,《麦收》如期放映了。另外,我特别想说的是那天下午,张老师在NGO的签名信旁边贴的那个通知,大概意思是通知大家在当天晚上临时召集一个创作论坛。我记得字号挺大的,很醒目。他开列了几个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比如说:“当代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群体是否社会意识大于个人意识?纪录片拍的是别人还是自己?”再如:“纪录片的私人性是否正当?私人领域被记录是否有上限或下限?”和“别人的隐私被记录,我们在遵循着自己的一套什么法则?”。那天晚上来得人很多,有易思诚先生,张亚璇女士,吴文光先生和他村民影像的作者们,还有NGO的几个代表,还有不少参加影展的导演及观众。讨论还是很热烈的。一个结果就是NGO们表示同意拿掉他们的签名信,当时普遍认为,也包括他们自己认为,其中的一些言辞未免武断和过激,像他们要求停止《麦收》的一切公开的放映及传播之类的;大家的依据是,这种说法有悖于言论自由。但是,我至今感到遗憾的是,那天晚上的讨论,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深入进去,并没有到达张老师所提出的问题的核心。我个人的原因肯定是前期的思考和准备不足的;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是说了“没有回头路可走”这类表决心的话。从那会儿起到现在,我一直努力在我的生活实践和拍摄中寻找这些东西。
几个月后,《麦收》去香港参加了“华语纪录片节”。就是张虹女士策划的那个。片子放映遭到了更加强烈的抗议。抗议者站在电影院的舞台上,像是那种左翼青年,手里举着红的调幅,上面写着“导演强暴弱势”“影展助纣为虐”等等。现场一度挺混乱的;后来来了四个港警维持秩序,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登记。最后,大家都做了让步,因为还有很多观众要看《麦收》,人家都是买票进来的。所以,买票的就和抗议的喊话,说这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后来,放映方采取了一些技术措施,把放映机向上抬高,让影像避开抗议者的遮挡;而抗议者也表示了适当的配合,原地就势坐在舞台上,这样,大家就相安无事了。第二天,香港的《明报》拿出了半个版面,做了详细的报道。意思还是说得挺客观的。这就是后来所说的《麦收》香港事件。
再几个月后,台湾政治大学的郭力昕先生,写了标题是“妓权、性道德、与自我正义”的评论文章;它的副标题是“再谈《麦收》与纪录片的伦理”。网上可以搜得到。他从“妓权”的角度,肯定了《麦收》在使性工作者“去污名化”的议题上所做的工作;他也批评了“中产阶级琐碎的道德洁癖”和“道德法西斯”的危害。在动笔前,他还专门从台湾电话过来,打在我手机上,证实了几个问题。再后来,我们也偶尔有邮件往来。转眼,一年过去了,直到上个月去台北的时候,才有幸头一回见到郭力昕先生。头发有些花白,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想不到,对于《麦收》这么质地粗糙的作品,他的文章却这么给力。
黎小锋:您怎样看待同行作品中的伦理问题?伦理问题如何影响到您的工作方法?
徐童:抱歉,小锋。我对于这个,还没有太好的看法。我可以推荐去看郭力昕的文章。
知识分子游民
黎小锋:摄影专业的教育背景对您的纪录片创作有何影响?
徐童:我的专业是学新闻摄影的,它对我帮助很大。因为不管怎么说,拍片子还是个技术性很强的事;这里头拍得好坏,高下之分一眼就看得出来。我并不是说科班出来的就好;我非常反对八股式的拍法。我是指一种游刃有余的,就是一种自由的境界。它能让我把遗憾降到最低;一段戏把它拍得鲜活,拍得淋漓尽致。有些业余作者一出手就能做到这个,但那毕竟是少数,那是需要天分的。就大多数人而言,还是多一些专业训练是对的。问题是一定要谨防一专业就八股,掉到里头就完了。所以,说到底还是要有些天分,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失望。
黎小锋:您是真正的自由职业,还是挂靠着某个体制单位?能否谈谈您的身份与您的纪录片创作的关系?
徐童:我没有单位。过着和游民一样的日子。我的片子就是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完成的。并且,我希望会这样持续下去。
黎小锋:您觉得自己纪录片的价值参照系在哪里?
徐童:如果说没有什么参照系,那就等于失去了基本的判断;但要具体说出个一二三,又确实很难。所以说,我所说的谈不上“纪录片的价值参照系”,只能说一些我喜欢的,现在还爱看的东西。小说应该是一块吧:中国古典的像《水浒传》到老舍;苏俄文学有托尔斯泰、契柯夫到《古拉格群岛》;法国的有新小说,像罗勃格里耶;还有拉美魔幻现实的《百年孤独》;两年前新出的后殖民小说《白牙》,英国的,我也非常喜欢。一时能想起来的就是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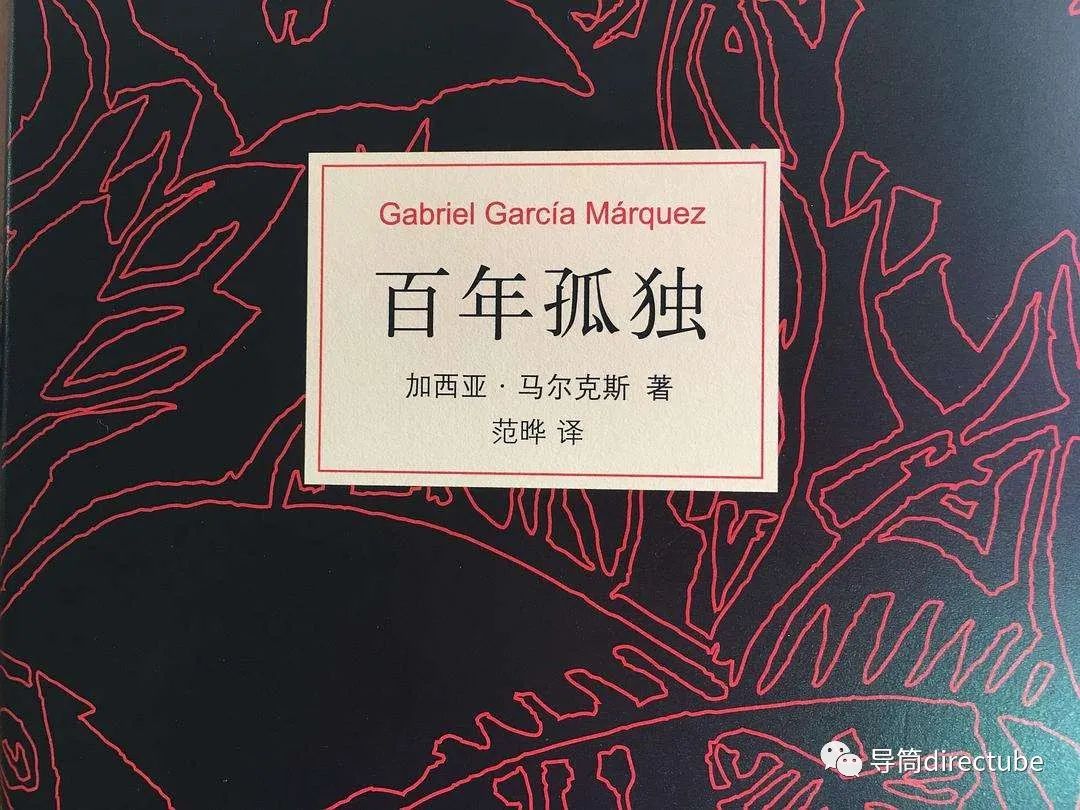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文 来源/导演帮(ID:daoyanbangwx)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6nwPMp85b-_ahIhybWgqw
内容由作者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附以原文链接
https://open.6pian.cn/news/6623.html全部评论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表情
添加图片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