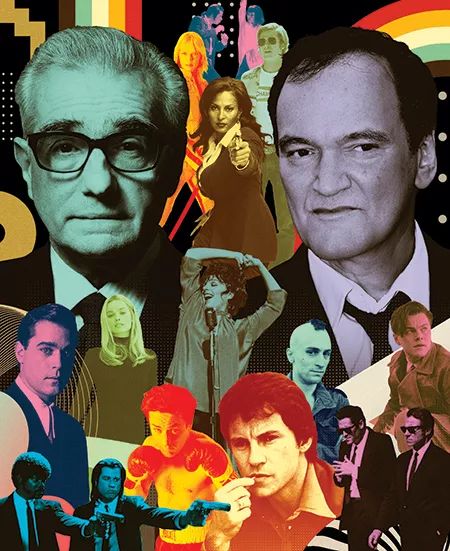
X
马丁·斯科塞斯和昆汀·塔伦蒂诺都是天生的故事讲述者,这不仅仅体现在他们的电影中,更是在他们对这个媒介的热爱当中。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年代,斯科塞斯出身自60年代中期第一波电影学校毕业生,而塔伦蒂诺撞上了90年代早期独立电影革命,但他们对电影的热爱和认识让他们成为了同类。
没有什么类型是他们不能驾驭的,不管是商业大制作还是小成本B级片,华丽的歌舞片或者黑色犯罪片,作者艺术片或者意式西部片。他们一辈子都在消化电影盛宴,而这也体现在了他们的电影中,在他们创造的角色中,在他们观察世界的镜头中。
今年对于两个导演来说都是爆发之年,塔伦蒂诺的新作《好莱坞往事》入选了戛纳主竞赛,影片被称为其最好的电影之一,获得了影评人和观众的集体盛赞,而斯科塞斯的新作《爱尔兰人》也在影评人届大爆,成为奥斯卡最大热门。最近两个导演在美国导演协会有了一次对谈,两人聊了关于导演,关于启发和暴力等等。
这是非常难得一见而且非常珍贵的对话,不仅仅因为这是来自两个大师间的对话,更是因为,这是来自两个全球最资深的影迷间的对话。
从怀尔德到希区柯克,从贝托鲁奇、帕索里尼到戈达尔、特吕弗,从佩金帕到莱昂内。
这篇不完全对谈纪录对于每个影迷来说都会是非常愉悦有价值的阅读体验。
马丁:我刚剪完《爱尔兰人》。
昆汀:我经常在剪到最后时,会什么都想要尝试一下。而当我们终于剪出来一个版本后,我晚上回到家,回想了一下,觉得这个版本太糟糕了,于是第二天又全部重剪。
马丁:最近这三个月我都这样,而且这部片我都没怎么试映过,主要是因为过去六个月我们一直在处理要把演员面容年轻化的特效问题。

▲ 《爱尔兰人》中德尼罗的年轻特效
昆汀:嗯
马丁: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而且非常紧张。影片最后结局本来是两个镜头,我又加了一个镜头,然后我想,“等下,我们需要这个中景镜头吗,还是说就留全景镜头就行”。所以我们做了很多尝试,然后一些朋友问,“你不是还拍了其它镜头吗”,“对啊,或许那个镜头更好”。但如果那样做,最后全景镜头的时长就会被改变。
昆汀:那我来问一个关于你这部新片的问题,《爱尔兰人》可能是你最长的电影之一了吧,好几个小时?
马丁:是的
昆汀:你是怎么处理节奏问题的呢?
马丁:有趣的是,我在剧本阶段的时候就想好怎么处理了。但情况比较复杂的是,我的处理方式让片长被拉长了,问题就在于这片是跟Netflix合作的。换句话说,我不太确定这片有没有必要是一部,比如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因为我完全可以把它做成四个小时。
昆汀:嗯嗯
马丁:所以我对这种发行方式意味着什么还是有点困惑。最终我在脑中跟自己说,“就把它当作是一部正常的电影,而如今我们可以把它拍得能有多长就有多长,每个镜头能有多长就有多长”,就像我们片中闪回部分的讲述者主角一样,他是一个在回忆陈年往事的81岁老人,所以长就很自然了。
昆汀:嗯嗯
马丁:昆汀啊,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会变得更容易陷入思考和沉思,更容易去回忆过去,也会更容易去思考角色对过去的感知。

▲ 《爱尔兰人》
我在剪辑过程中就是这么感受的,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放手去做吧,能多长就多长,之后再给一些观众看看,看他们忍不忍受得了”。因此我们一直在说“这样试试,那样试试”,而且我们现在正在处理的特效问题也给了我们充分的时间。
昆汀:明白了
马丁:影片节奏其实很安静。虽然也有暴力,有幽默,但讲述的方式又不太不同。其实还是那句老话,你拍得越多,需要学习的就越多。
昆汀:你知道吗,马丁,我跟你说说我现在正在处理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它可能会提出一个关于你和电影的好问题。我现在在写一本书,其中有个角色经历过二战,看过了太多流血伤亡。如今他已经回到家,大概是50年代的样子,他发现自己对电影完全免疫了。在经历了那一切后,他觉得电影非常幼稚。因为在他眼里,好莱坞电影就是电影的全部。但后来,他开始听说很多外国电影,费里尼,黑泽明…
于是他想,“或许他们的电影能比这些好莱坞俗套货要好点”。
然后他就彻底被这些电影吸引了,其中一些他很喜欢,另一些他很讨厌,还有一些他看不太懂。但他知道他对眼前的这些电影很感兴趣。
所以我现在的状态是:为了这个角色,会去重看很多外国电影,或者第一次看那些大名鼎鼎但我一直没机会看的电影,但是是从这个角色的视角去看。我看得很开心,但我会想,“这个角色会怎么想呢,他觉得好不好看呢”。我经常会找这样的借口让自己去看电影。所以我想问的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把视线从好莱坞电影,转移到那些你经常在书中看到的外国电影,变得更有冒险精神?
马丁: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人生最开始的那六七年我都住在皇后区,然后因为房东问题,我父亲把我带回了小意大利区,那是他和我母亲出生的地方。当时那个环境就像莱昂内尔·罗戈辛的《鲍尔瑞大街》。但在那之前,可能是因为哮踹,我父母会经常带我去看电影。所以我看了《阳光下的决斗》,那是我看的第一部电影。接下来是《绿野仙踪》,《秘密花园》,以及一些黑色电影比如费斯特的《威胁》。你看过《威胁》吗?

▲ 《威胁》
昆汀:看过啊,我超喜欢《威胁》
马丁:还有罗伯特·怀斯的《月宫浴血》,威廉·A·塞特尔的《维纳斯的一触》。我们当时有个小电视机,爷爷奶奶会在周五到我们家来看电视,因为每周五晚都会给意大利社区放意大利电影。当时放过《偷自行车的人》,《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以及《战火》。当时我只有五岁,就目睹了爷爷奶奶看《战火》看得泪流满面的场景,我意识到电影中的语言跟爷爷奶奶说的语言是一样的。

▲ 《战火》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还有另一种电影艺术(Cinema)的存在,而那并不是大众电影(Movies)。
马丁:我看的第一部关于好莱坞的电影是《日落大道》

▲ 《日落大道》
昆汀:哈哈哈,那是好莱坞的黑暗面
马丁:从某种角度来说,当时的好莱坞电影都被审查了,真相通过另一种形式、代码、甚至文化来传递。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电影不比我看过的那些欧洲电影重要。但当我看那些意大利电影的时候,有某种东西影响了我,永远改变了我。这些外国电影,给我了一个看世界的窗户,它们让我对这个世界感兴趣,而不仅仅是我住的那个意大利裔美国人的西西里社区。
昆汀:所以这有没有让你去探索去寻找纽约的那些在你邻里之外的电影院?
马丁:不止这样。当时外国电影大规模涌入美国,只是没有在我住的那个城区放映
昆汀:是的,我懂你
马丁:当时很可怕的,纽约有很多糟糕的城区,你必须跟朋友们结伴同行。你有没有去过42街,当时所有电影都在那儿放。
昆汀:我从没去过。其实我第一次去纽约,是为了给《落水狗》选演员。你要知道,我从第一次听说纽约这个地方,第一次看纽约电影,我就一直想去纽约。但我小时候从没有人带我去,而当我长大了又没钱去。当时我们在给《落水狗》选演员,哈威·凯特尔就说,“我不敢相信我们不给纽约演员一个机会”。我就说,“我们没钱去纽约啊”。然后哈威就说,“我来找一个选角导演来安排,就一个周末,你和劳伦斯·班德(《落水狗》制片人)一起去”。所以我们就这样去纽约待了一个周末。我们走出机场时还是早上,我们开着车穿过纽约抵达酒店,我记得是五月花酒店…
然后我就想说,“我这辈子都想去时代广场电影院,所以一旦我们工作完成,我就要去时代广场,随便看一部他们在放的电影”。然后哈威说,“昆汀,你别去,一周后你再去都行,但你不能明天就去,你对于纽约来说太嫩了”。
马丁:哈哈哈哈哈哈。他说得对啊。你知道在50年代的时候,去那种地方要跟四个朋友一起去。他们那个时候什么电影都会放。虽然没有跟性爱相关的电影,都是常规的好莱坞电影。我们那个时候常去,尽管那是个很危险的街区。他们那个时候放的都是,鲍威尔和普雷斯伯格拍的《难以捉摸的海绿》,然后同场放映的是柯克·道格拉斯主演的《尤利西斯》。街对面在放《火海浴血战》和《勇冠三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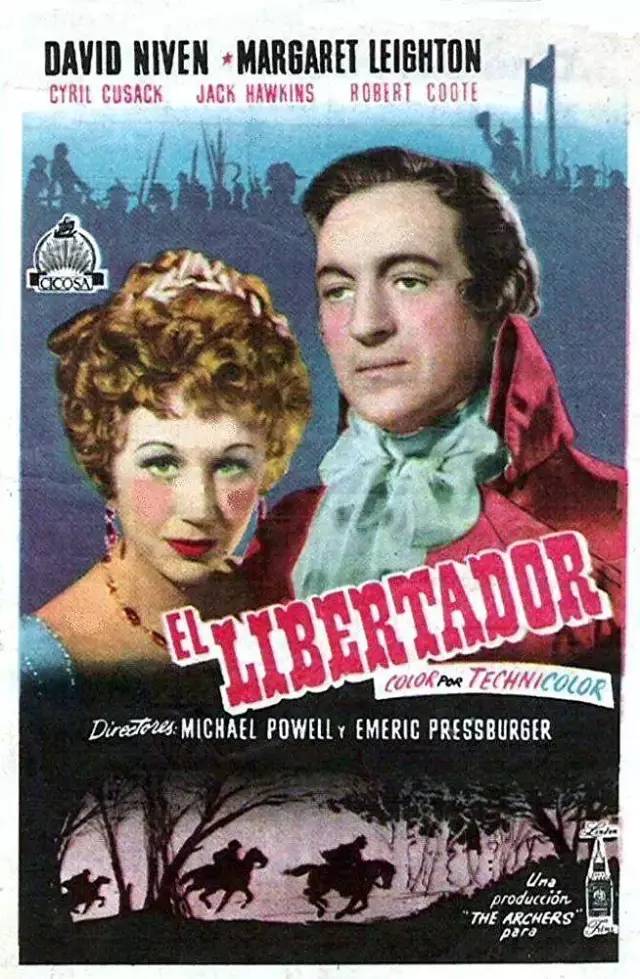
▲ 《难以捉摸的海绿》
昆汀:嗯嗯
马丁:一部是刘易斯·迈尔斯通执导的,另一部是亨伯斯通。两部都是Technicolor的电影,但他们竟然放的是黑白版!
然后我们进场看这两部片,二楼楼厅还有人打架,各种吵闹,但我们还是坐下来看完了两部片。当时所有的拷贝都是黑白的,《铁血金戈》也是黑白的!
昆汀:哈哈哈哈哈,其实我在洛杉矶也有过类似经历,在百老汇大街上的Cameo和Arcade电影院。那个时候这两个电影院都是通宵放映。我记得82年的时候在那里看了Ralph De Vito的《死亡收集者》,乔·佩西的第一部电影。
马丁:是的,我们就是因为看了这部片才把乔·佩西找来演《愤怒的公牛》。

▲ 《愤怒的公牛》
昆汀:我当时听说Arcade电影院要放这部片,就在《愤怒的公牛》公映后一两年,我就想说,一定要去看,但去看的唯一办法只有凌晨四点场。还有一场是晚上八点,但我才不愿意那个时间去…
马丁:《死亡收集者》,罗伯特·德尼罗在CBS电视台看了后跟我说,“我在电视上看了部片,主演很有意思”。所以我们要来了拷贝。
昆汀:那是部好电影,当我终于看到时,我就想说,“哇,这其实是剥削版的《穷街陋巷》”。
马丁:哈哈哈哈哈你说得对。不过现在这种有自己拷贝库存的电影院都消失了,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昆汀:其实我在洛杉矶有一家这样的电影院,我们经常放你的片,都卖得不错。
马丁:谢谢
昆汀:而且我们只放35毫米或者60毫米,我们有一整个箱车的拷贝库存。当我们说起纽约电影人时,我第一个想起的是你,马丁。我还会想起西德尼·吕美特,想起伍迪·艾伦。而且你是60年代纽约新浪潮的一份子。60年代那个时候,像你还有吉姆·麦克布莱德,雪莉·克拉克以及布莱恩·德·帕尔玛。我对“纽约新浪潮”这个概念非常感兴趣,你们又是或多或少受到法国新浪潮的影响和启发,只要给我一个摄像机,我就能把它架在汽车上,然后就可以开拍了。

▲昆汀在洛杉矶的电影院
马丁:或者放在轮椅上,或者让摄影师拿着摄像机坐在轮椅上,推拉镜头就这么来的。
昆汀:是的
马丁:纽约这个其实是来源于战争后那个时期,当时纽约很少有人拍电影了。制片厂系统当然还有,那是工厂批量生产的。有了能为你提供一切的制片厂,电影人们没有任何去纽约的理由了。所以我觉得真正改变一切的是,新现实主义,让大家到真实的现实的场景中去拍摄。
昆汀:是的
马丁:他们当时拍摄的纽约非常棒,乔治·库克,《双重生活》,所有这些电影,都真正的把摄像机带去了街头。
昆汀:嗯嗯
马丁:尽管当时纽约还不是一个电影拍摄圣地。交通拥堵,所有人都赶着去上班,他们会在摄像机前走来走去,而且坚决不听你指挥。所以当时他们把摄像机藏在各种地方,结果就变成了美国先锋派,乔纳斯·梅卡斯在50年代中期推广的那些。Amos Vogel,乔纳斯·梅卡斯,雪莉·克拉克…
昆汀:是的
马丁:雪莉·克拉克《冷酷的世界》就是在街头拍的。但真正的突破,还是卡萨维蒂的《影子》。

▲ 《影子》
昆汀:绝对的,他是这方面的教父
马丁:我当时看完《影子》,然后我对朋友说,“这下我们没有任何借口了”。只要你有想说的想表达的,他们就能拍出来。他们当时用的是16毫米Éclair摄像机,更小也更轻便。那是决定性的,因为我们发现这样就能拍出来,不需要西海岸那些庞大的机器。
昆汀:纽约新浪潮最有趣的点,无论是和新现实主义还是和法国新浪潮作对比,尤其是法国新浪潮,他们总是在同一个城市中拍摄。你可以想象,安娜·卡里娜在戈达尔《随心所欲》中的角色随时都可能会遇到特吕弗《射杀钢琴师》中的钢琴师。那是绝对可能发生的。
马丁:说得太对了
昆汀:但是纽约新浪潮,大家都呆在自己的那个城区。但也因此让我们看到了纽约的不同面。比如你不会想象《冷酷的世界》中的角色会遇上《谁在敲我的门》中的角色,或者布莱恩·德·帕尔玛《帅气逃兵》中那些格林威治的嬉皮士。他们不可能存在于同一个画面中。

▲雪莉·克拉克《冷酷的世界》
马丁:绝不可能,不同城区就是不同国家。我们当时绝不会去110街,我也不知道那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我也不关心。那是另一个世界。1960年我去纽约大学时,我从我住的地方左转然后步行几个街区就到了另一个星球。但这也平衡了我的创作。比如在《穷街陋巷》中,我们就能看到之内和之外两个世界。

▲ 《穷街陋巷》
昆汀:我最近刚看了《谁在敲我的门》,让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我知道你是约翰·福特《搜索者》的死忠粉,所以片中有一整场戏是哈威·凯特尔聊《搜索者》。
马丁:我知道,我必须这么做
昆汀:那是整部片我最喜欢的一场戏。其实在整个纽约新浪潮中,你的电影是“最新浪潮”的,看起来很像法国新浪潮。
马丁:是的,黑白嘛。但你说得对,肯定是有法国新浪潮的影响,其实还有贝托鲁奇,《革命前夕》就像原子弹一样打破了一切。还有帕索里尼,《乞丐》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我特别喜欢他们在胶片上打孔的方式。

▲ 《革命前夕》
昆汀:嗯嗯
马丁:当你看着胶片剪辑每一帧时,那感觉太棒了,你可以直接在胶片每一帧的边上剪切,你可以保留两帧的同时再剪掉一帧。他们当时就这么做的,所以我们也照着学,跟着实验。我们当时在纽约大学拍短片就会遇到各种剪辑问题。我们当时会说,“特吕弗说过,他剪片子的时候先这样剪,重剪的时候再那样剪”。然后我们的老师,Haig Manoogian,会跟我们说,“那是扯谈,他绝不会那样做”。后来我们有个镜头,老师说,“听着,你可能会因为某种原因拍某个镜头,但当你在剪辑过程中会发现这个镜头并没有用”。这就像库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中的巨型黑石头,你摸了一下黑石头,然后拍一个跟那场戏完全无关的镜头。
昆汀:嗯嗯
马丁:但那个镜头如果换个地方就有了另外的意义。老师说,“你们会了解到一个镜头的真正价值”。这个镜头有了自己的生命轨迹,你能在16毫米或者35毫米的胶片中清晰看到这个轨迹。
昆汀:你提到这个太有趣了,因为我和我剪辑师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我们剪辑时作弊然后还没人发现,但其实显而易见。
马丁:太显而易见了。在《禁闭岛》中有场戏,莱昂纳多的角色在一个疯人院询问一个女人,一个看起来很友好的女人,谈论她如何用斧头砍死了她丈夫。有个她的过肩镜头,非常希区柯克式的镜头,她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然后放下杯子。接着镜头切回莱昂纳多。这个过肩镜头中,她似乎拿起了杯子然后又放下。但其实她手中根本没有杯子。

▲ 《禁闭岛》
昆汀:啊哈,哈哈哈哈
马丁:那个镜头其实是她在试戏在排练时拍的镜头,但剪辑时我说,“我们保留这个镜头吧”,你以为她拿起了杯子,但其实并没有杯子,这就是整部电影在讲的事啊!什么是真实的,甚至是不存在的,什么是想象的。
昆汀:这太完美了
马丁:是的。那个镜头重获了自己的生命。那些你本以为决不可能剪到一起的镜头,其实可以。而那些你本以为剪到一起会很漂亮的镜头,结果却成了灾难。
昆汀:我基本上快结束《好莱坞往事》的宣传了,这段时间我被问得最多的就是,“你觉得最难拍的是哪一场戏?”我觉得我真正的回答可能是,如果我有一个大场景准备好要拍,比如当时是周二,我们周三拍,而我拍这部电影有一半的原因都是为了拍这场戏,这场戏我已经在自己脑中看过无数遍了,而现在,如果我不能拍成我脑中那个样子,至少只有我知道自己失败了。

▲ 《好莱坞往事》片场
马丁:的确是这样
昆汀:所以就像是我自己在检验自己的能力。我能达到自己的要求吗?我有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优秀?而在拍这些戏之前的那几天,我整个人都无比焦虑,因为我希望这些戏能像我脑中想象那样好,我就像站在山脚下,望着一座登天高峰。我知道一旦当我开始攀爬,我会没事的,但我得开始着手攀爬,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
马丁:哈哈哈哈哈哈太对了,完全的焦虑,恶梦,所有这一切。每天早上到片场的过程,抱怨,争执。最终还是得开拍。
昆汀:这些早上的我是最恶毒的。我会跟所有人说,“别打扰我”。
马丁:“别靠近我”,哈哈哈哈哈。我走出拖车,我对所有人都很友好。我走进拖车,里面坐着我的助理和制片人,他们都理解我。当摄影指导走进来,他们也都理解我。而我经常抱怨的是交通拥堵,或者我牙痛,或者其它什么。“这鬼地方简直没法工作了”,你懂的。
昆汀:是的
马丁:但我经常在各种场合提到的最神奇的事,就是将脑中的概念付诸实践的过程,通过所有这些设备,器材,镜头,如何将我们脑中的梦变成现实。这简直太稍纵即逝了。一旦我们开始将其变成现实,我们会逐渐损失最初这个梦的模样、最初想要表达的东西。非常困难的过程。
昆汀:这其实是很有趣的双刃剑,也是为何我们会如此焦虑。一方面,我们脑中有一部完美的电影,但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想要那部电影,我们想要创造一部更好的电影,因为我们没法拥有脑中的那些演员。
马丁:就是这样
昆汀:你的电影可以用音乐用剪辑用其它东西让观众“啊”“哇”,但必须还要有生命有心跳。
马丁:是的
昆汀:但我还是希望观众能有“啊”和“哇”
马丁:我明白,所以就有了所有这些紧绷的张力。然后人们会说,“那如果你那么讨厌拍电影的话”,我并不是讨厌好吗
昆汀:那不是讨厌
马丁:那就是我们在做的事
昆汀:这其实是我生命中最精神充沛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恐惧和焦虑。
马丁:天啦。但你要知道,在既定条件下,你已经做到最好了,你的摄影指导,你的演员,还有天气,你的感受,取景地,拍摄周期表。除非像有些人,会跑回去补拍重拍。
昆汀:我觉得那是作弊。你必须在既定时间内,在所有人在场时,试图把你想做的做完,就算会拖延几天…
马丁:是的,就像职业拳击赛一样
昆汀:任何人都能做没有限制的事
马丁:是的,就像职业拳击赛,有几轮比赛,每一轮都有既定时间,你需要坚持到最后一秒,然后就结束了。我有时的确会多拍几天,好像是在拍《无间道风云》的时候。当时是,我们拍了一半时,改动太多了,我一边拍,一边跟编剧团队改剧本。一切都变得太复杂,以至于有一天,我的场记跑来问我,“这场新加的戏是准备放在什么地方”。我说,“随便放在什么地方吧”,哈哈哈哈,“后期的时候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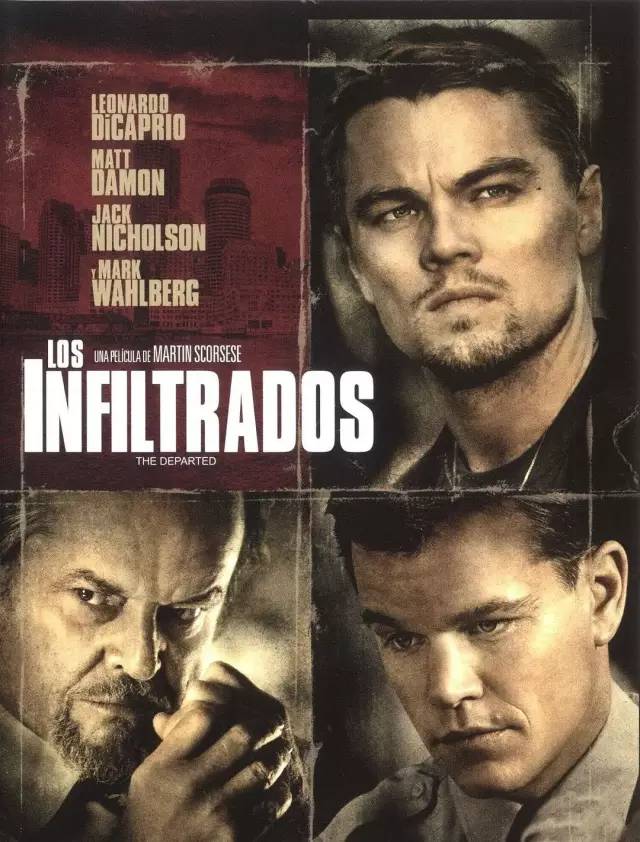
▲ 《无间道风云》
结果我跟我的剪辑师塞尔玛·斯昆梅克在后期整理素材时,感觉就像在试图控制六头野马。当最后终于整理出来后,我们才清楚,哪些是要的,哪些是不要的。
昆汀:说得很有道理。关于我刚刚提到的在拍摄某场重头戏前的焦虑和恐惧,我想你在拍摄《出租车司机》的高潮戏前也跟我一样吧
马丁:拍《出租车司机》的每天我都那样。本来计划是40天的拍摄,结果我们拍了45天,他们因此对我们非常不满,各种电话连环夺命Call,愤怒,不满,简直是恶梦。不得不说,你在那场戏中看到的那种能量,我精心设计过的这场高潮戏,拍摄过程有带入了这种愤怒情绪的。
这让我们倾尽全力,就像打了一场战争,一直在斗,在吵,在争,一直到最后。就像你做的所有事都是在争取得到你想要的镜头。最终我们其实是在跟时间作抗争。
但正因为如此,赋予了整部片某种能量,我们当时都处于突击模式。

昆汀:完全理解。尤其是那场宣泄动作戏,从某种层面来看有种歌剧风格在里面,甚至日式风格。
马丁:是的是的
昆汀:但从另一种角度看又极其写实,比我看得很多电影都真实的观影体验。结局一定是宣泄式的,将所有元素结合到了一起。这个人一直在自己的公寓里然后突然这样的结局,就像是燃料终于和炸弹遇到一起了
马丁:是的,其实保罗·施拉德写这个的时候是很私人的。给我的感觉是,
他希望能更日式,更风格化。他说希望墙上能有更多血。
我就跟他说,“我又不是市川昆,这电影也不是黑泽明的《椿三十郎》”。
我看过这些电影,我也很爱这些电影,但每当我试着做出那样的东西,最终出来的都是另一种东西。因为在我长大的地方,当我看到暴力或者暴力威胁,那都是真枪实弹的。
非常严重,而且是有后果的。不管是给你一巴掌,或者,一声巨响,你可能下一秒就死了。所以我是按照真实可能发生的去设想去拍的。
昆汀:我记得你说过,你很困惑的是观众觉得这几场戏是情绪宣泄式的,但是对我来说,似乎本来就是情绪宣泄。
马丁:我并不知道这个。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我们都想拍出来的项目,因为这些感受我们都有。与社会的脱节,愤怒。当然我们不会像主角特拉维斯那样越界,但我们能理解那种情绪。
昆汀:明白明白,所以你当时根本没想到这部电影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马丁:我以为没人会看这部片。

▲ 《出租车司机》
昆汀:所以我对《出租车司机》的最大疑问是,这部片最终哥伦比亚愿意拍,是不是因为它其实很像迈克尔·温纳的《猛龙怪客》
马丁:制片人朱莉娅·菲利普斯和迈克尔·菲利普斯当时刚刚凭借《骗中骗》拿了奥斯卡最佳影片,他们当时力挺这个项目,跟哥伦比亚的人不停交流,最终才成型。但哥伦比亚并不想拍这个片,后来的每一分钟他们都在强调这一点。
昆汀:噢,真的吗,哈哈哈哈
马丁:真的是每一天。尤其是我把成片放给他们看,他们彻底愤怒了,结果拿到了X分级。我经常说的一个故事是,我跟朱莉娅和迈克尔一起去哥伦比亚开会,他们看着我,我走进去,拿出纸笔准备做笔记,他们说,“要么你把片子剪成R级,要么我们自己动手剪”。
昆汀:天啦
马丁:我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无能为力。我面对的是一个巨型黑石,而只有朱莉娅和迈克尔支持我。所有这些会议,面谈,以及和分级机构拉锯。那场枪战戏,我不知道还能怎么拍。我知道它是创造出来的影像,但不知道它能产生的影响。所以最终我还是剪了两个镜头。那种暴力宣泄是真实的啊,我在看《日落黄沙》时就感受到了。
昆汀:我在看《出租车司机》最后也感受到了。
马丁:《出租车司机》中的角色80%或者90%都是德尼罗一个人。
昆汀:是的
马丁:他的表情,他的眼神

▲ 《出租车司机》
昆汀:有趣的是,你,德尼罗和施拉德,你们选择了通过特拉维斯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德尼罗进入了特拉维斯的视角,这是第一人称的角色研究。所以如果他是一个种族歧视者,那我们就是一个种族歧视者的视角。
马丁:是的
昆汀:但是当特拉维斯只身面对那些皮条客时,我是站在特拉维斯那边的。如果我们不需要支持他的话,那也就没必要让妓女角色是个未成年了。
马丁:你说得对。那是施拉德在剧本中就设定好了的,而哈威则即兴创作了一些台词。
昆汀:如果你足够有才华有能力的话,你会创造出一些意外的好东西。
马丁:是的
昆汀:有时候如果我在一个电影书店,我会找那种影评论文,写的关于我不是很了解的导演和作品。我会看这种文章,然后让我开始了解这个导演和他的作品。有次我在巴黎待了一个星期,当时我们在法国拍《无耻混蛋》。在巴黎的Champollion街上有一家非常棒的电影书店,那条街上也有很多小电影院,我并没有看过很多约瑟夫·冯·斯登堡的电影,所以我在书店里面拿了一本关于他的书,我太喜欢了所以又拿了一本,最后我还买了他的自传,写得荒谬可笑,我一个字都不信,但我非常喜欢,很好笑。
马丁:哈哈哈哈哈我知道
昆汀:真的是一字不信。后来我开始看他的电影,然后我发现自己受到他电影中艺术指导的启发。
所以我现在每部电影都会学约瑟夫·冯·斯登堡这么做几次。在《无耻混蛋》中就专门设计了一个约瑟夫·冯·斯登堡式的镜头,你把整个场景都设计好,然后推拉镜头跟着角色走过整个场景,所有的烛光、杯子、钟、灯光。
马丁:我喜欢推拉镜头跟着人物的动作。我记得是戈达尔的《随心所欲》,男人说“我想要一张朱迪·加兰的唱片”,
然后女主穿过唱片店,找到唱片,然后镜头又跟着她回来。这就像是音乐编排一样的客观性,而且还有一种对角色灵魂状态的客观性,不想靠得太近。

有一个东西是我在很多电影中都尝试捕捉的,但仍然没有成功,不过没关系,尝试已经很有意思了。在希区柯克的《艳贼》中有个镜头,女主要准备射杀她的马,她拿着手枪奔跑,镜头跟着她的手,然后跟着她肩膀。镜头一直在运动,跟着她的手运动时,地面是倾斜的。我几乎在每一部电影中都尝试过这么拍,但最终都像推拉镜头,显然希区柯克不是这么拍的。

▲ 《艳贼》
马丁:希区柯克的镜头是浮动的,但我无论如何就是做不到,不过尝试过程太有趣了。
昆汀:我在拍摄最近三部电影的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而在《好莱坞往事》中我认为我终于做到了。我想做的甚至都不是来自于电影本身,而是萨姆·佩金帕《比利小子》的预告片,克里斯·克里斯托佛森在每秒24帧的画面中开枪,詹姆斯·柯本在隐匿处,然后就是枪战,然后镜头切到中枪的角色,慢动作。

▲ 《好莱坞往事》
然后镜头又切回克里斯·克里斯托佛森,24帧,砰!砰!砰!然后镜头切到他倒地,120帧。
马丁:哇
昆汀:我试着模仿这种方式。在《姜戈》就试过,但失败了。在《八恶人》的枪战戏也试过,成功了,但跟我想要的不一样。
马丁:哈哈哈哈哈哈哈
昆汀:但是在《好莱坞往事》布拉德·皮特揍人那场戏中,我终于成功了。他揍人的镜头是24帧,被揍的那个人倒在沙土中的镜头是120帧。
马丁:那太棒了,这样一来沙尘就跟显眼了,你做得太好了
昆汀:是的
马丁:我总是想拍沙尘
昆丁:以及满脸的血印
马丁:棒极了,我总是想这么做,但又做不到。莱昂内《西部往事》中的那个墨西哥小男孩,当他得知哥哥被吊死了…

▲ 《西部往事》
昆汀:啊对对对
马丁:他哥哥本来在他肩上,然后小男孩在慢镜头中倒地,被包裹在沙尘中。我试过这么拍
昆汀:根本拍不出来
马丁:我甚至在《基督最后的诱惑》中试过,也是没成功。我们当时在摩纳哥,哈威跟我在一起。不知道是不是跟沙尘有关哈哈哈。
昆汀:肯定是的,那种沙一定得很轻才行,需要那种西班牙沙土,阿尔梅里亚沙土。
马丁:西班牙吗,哈哈哈哈太好笑了。
原文来自美国导演工会DGA
内容由作者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附以原文链接
https://open.6pian.cn/news/4633.html全部评论

分享到微信朋友圈
表情
添加图片
发表评论